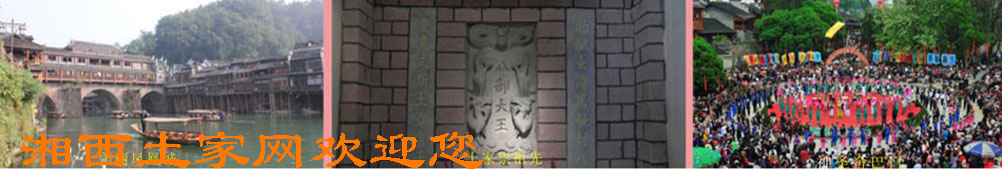湘西彭氏土司主的早期字辈及其他(上)
彭承忠
字辈,也叫字派,是中国姓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定血源、识代次、明伦理、分尊卑、利交际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对皇家、大族的世系曾作记载,对西南土司的传承也有涉及。我们可以从明永乐以前的史籍文献如《宋史》(以下简称“宋史”)《资治通鉴》《九国志》《宋会要辑稿·蕃夷》《江南野史》、溪州铜柱铭文(以下简称“铜柱”)等史料中,找出湘西彭氏土司主的早期字辈:
1.宋史(列传·卷252,下同):
又有溪州刺史彭士愁等以溪、锦、奖州归马氏,立铜柱为界。
铜柱:
1)师杲为父输诚,束身纳款。
2)彭师佐、彭师裕、彭师榳、彭师晃(其任职情况略)。
说明:“师”是司主彭氏字辈,比彭士愁小一辈。
彭士愁的字辈,史书未载,但通过历史学家对《资治通鉴》(卷267)关于“彭彦章”的记载“章,玕之兄也”的纠错中可知为“彦”。章钰(1864年—1937年)校刊的胡三省(1230年—1302年)之《资治通鉴音注》(中华书局,中华国学文库,2013年版,卷十一)里对《资治通鉴》(卷267)中“彭彦章”的注,为“章,十二行本‘兄’下有‘子’字,孔本同”。这里的“十二行本”是指宋刊本《资治通鉴》九种的一种,刊印于宋高宗绍兴二至三年(1132年—1133年),“孔本”指孔天胤(1505年—1581年)校刊的《资治通鉴》明刊本。也即在南宋建立不久,就有人纠正《资治通鉴》(卷267)之“彦章,玕之兄也”为“彦章,玕之兄子也”。元代认可宋代之纠,明代亦认可其纠。因此彭彦章,是彭瑊的侄儿,是“彦”字辈。又,元朝史学家欧阳玄在江西《珠溪彭氏族谱序》(见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七)中记“(彭)玕兄弟五人,为太尉者四,子十一,人人皆检校大傅大保,六曹尚书,诸镇刺史,孙二十七人,相继登进士为显宦”,此谱记彭玕“第五子彦昭”“彦昭生师遇”“太尉(即玕)子以‘彦’行、彦昭公十五子皆以‘师’名”,说明“彦”是彭玕之儿子们的字辈、“师”是其孙辈的字辈。
而彭瑊为彭玕之弟,则见北宋路振的《九国志》卷十一“彭玕传”:“玕,吉州庐陵人……兄邺、弟瑊……”。
永顺、保靖彭氏族谱记载彭士愁又名彭彦晞,为“彦”字辈,与彭彦章、彭彦昭同字辈,是符合史实的。
2.宋史:
1)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知溪州彭允林诏为溪州刺史。
2)以溪州团练副使彭允足为濮州牢城都指挥使,溪州义军都指挥使彭允贤为卫州牢城都指挥使。
3)允足等溪峒豪酋据山险,持两端。
4)溪州刺史彭允殊上言:刺史旧三年则为州所易,望朝廷禁止。
铜柱:
“彭允臻、彭允瑫”“彭允强”“彭允会”(任职在此略)。历三四代,长千万夫。
说明:“允”是彭氏的字辈;两相结合,可确定“师”字辈后为“允”字辈;“三四代”是彭瑊、士愁、师杲和师裕、允臻和允瑫。
3.宋史 :
1)以下溪州刺史彭允殊为右千牛将军致仕,以其侄彭文勇为刺史。
2)上溪州刺史彭文庆来贡水银、黄蜡。
3)溪峒团练使彭文绾送还先陷汉口五十人,诏授文绾检校太子宾客,知中彭州。
4)溪州刺史彭文庆率溪峒群蛮来朝。
铜柱:
彭文绾、彭文傥、彭文雅、彭文威、彭文仙、彭文胜(所任职在此略)。
说明:“文”是彭氏字辈,比“允”小一辈。
4.宋史:
1)辰州诸蛮攻下溪州,为其刺史彭儒猛击走之。
2)儒猛乃奉上所略民口、器甲,诏辰州通判刘中象召至明滩,与歃血要盟,遣之。诏以仕汉为殿直,儒霸、儒聪为借职,赐冠带、缗帛。
3)儒猛攻杀文绾,其子儒索率其党九十二人来归,补儒索复州都知兵马使。
说明:“其子儒索”的“其”是指“文绾”,所以“儒”是彭氏的字辈,比“文”小一辈。
5.宋史:
1)刺史彭儒猛亡入山林,执其子仕汉等赴阙。
2)儒猛言仕汉逃归,诱群蛮为乱,遣别子仕端等杀之。
3)儒猛死,仕端以名马来献,诏还其马,命知下溪州,赐以袍带。七年,遂以其弟仕羲贡方物。明道初,仕端死,复命仕羲为刺史,累迁检校尚书右仆射。自允殊至仕羲五世矣。
说明:“仕”是彭氏字辈,比“儒”小一辈。
6.宋史:
1)仕羲有子师宝,景祐中知忠顺州。
2)与其子知龙赐州师党举族趋辰州,告其父之恶,且言仕羲尝杀誓下十三州将,夺其符印,并有其地,贡奉赐予悉专之,自号如意大王。
3)仕羲岁奉职贡。……为其子师彩所弑。师彩专为暴虐,其兄师晏攻杀之。
4)其后彭仕诚者复为都誓主。元祐三年,罗家蛮寇钞,诏召仕诚及都头覃文懿等至辰州约敕之。
5)知誓下保静州彭儒武、知永顺州彭儒同、知谓州彭思聪、知龙赐州彭允宗、知蓝州彭士明、知吉州彭儒崇。
6)辰州言,归明保静、南渭、永顺三州彭儒武等久欲奉表入贡。
铜柱:
彭如喜、彭如兴、彭如武、彭如聪、彭如品、彭如熹、彭如亮、彭如会、彭如权。
说明:此“师”字辈以及“彭士明”的“士”“彭思聪”的“思”是同一个辈分,是字辈“思”另写,为“仕”的下一辈,“彭儒武”“彭儒崇”的“儒”和“彭如喜、彭如兴、彭如武”等的“如”是一个字辈,比“思”小一辈,应是“汝”的误记,均因是同音字、记者未细辨所致。
另外《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记载,彭儒武欲奉表入贡的时间是绍兴四年,绍兴即南宋高宗年号,为公元1134年。
7.宋史:
允林卒,其子师皎代为刺史。
说明:这里的“子”应是脱脱(元代修宋史的主编)及其助手们把“叔”理解错了或写错、印错了。不然,与下文的“彭允殊……致仕……其侄彭文勇”的代次字辈相矛盾,在同一时期同一族内不可能“允”字辈后面既是“师”字辈又是“文”字辈。若“允”下为“师”字辈,则与铜柱“师杲为父输诚”相矛盾,因师杲之父彭士愁不是“允”字辈,而是“彦”字辈(前已述及)。而且若师皎是允林之子,则可以直接“袭”任刺史,不必“代”为刺史,只因允林之子文勇太幼,才由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先“代理”“摄事”,所以师皎是允林的“叔”而非“子”,后面由允林之弟允殊正式接任刺史,则是兄终弟及,符合袭任一般规定,允殊卒后由其侄文勇接任,是世袭职务再回嫡长系。其袭任程序都是符合汉制及其文化传统的。
湘西彭氏土司主的早期字辈及其他(下)
彭承忠
综上,从溪州铜柱和明永乐以前的史籍文献中,可知湘西彭氏土司主的早期字辈是:彦、师、允、文、儒、仕、师(思)、儒(汝)。经调查,这八个字辈与江西彭氏(彭玕的两支后裔)的“彦、师、允、文、儒、仕、思、汝、忠、义、大、公、世、远、长、贻、谋、景、美、利”的前八个字辈相同(《来字号》谱及宜春、于都谱及字辈总表,由赣州彭氏提供,有多房多支的字辈如此)。即便是彭师宝的“师”、彭儒武的“儒”,不是“师”“汝”的另写,而是“彦师允文儒”的“师”“儒”字辈,加上彭允会彭允强的“允”,也说明从五代至南宋初这230年左右的时间里,湘西彭氏土司主的字辈与江西几支彭氏的字辈是相同的,后由于年代久远、关山隔阻、战争严逼而忘了或失了后续字辈,而从“允”开头再取用旧字辈,仍能证明,湘西彭氏土司主来源于江西,他们的自述值得采信。
另外,北宋末和南宋以后,湘西彭氏司主更因为与当地土著的深度交融而入乡随俗取土著名字作为常用名,如彭师宝的儿子彭福石宠(应有以字辈取的书名,为“儒”或“汝”字辈,但失记录),有专家研究“福石宠”是土家语“服兹冲”的另写,意思是“本地人的王”,即“土王”,本地人的王。细分析“本地人的王”,也含有此王不一定就是本地人而是外来的意思,不能如有的研究者理解为只是本地人,而否定其源自江西。
最后,说说对《楚纪》之《彭瑊》条“辰州上溪州人。其先出自汉彭宣之裔,厥后有彭构云者,唐天宝中以逸士征、不仕,号其里曰征君乡;有彭玕者,仕朱梁为龙韬将军、安定王;瑊承遗烈,仕唐为检校司徒、辰州刺史,开平四年,吴敖骈围赤石,瑊调所部征之,被执不屈而死,阖门受害,乡巷哀而壮之;五季时有彭仕然者、亦曰彭士愁,力抗马希范,以保障其乡,树铜柱以效伏波;嗣孙彭儒猛纳款于宋……彭氏所居,有堂翼然,表以世式,允示家传……”的理解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这里“阖门受害”是彭瑊满门受害没有后代了,从而认定彭士愁不是他的儿子,进而认为湘西彭氏土司主不是来自江西而是自古就是本地土著。这种对“阖门”的理解是不准确的。“阖门”,是指彭瑊原留守在江西赤石的一些老小,而未包括彭瑊在辰州为刺史时所带去的或在辰州及上溪州新有的妻儿老小。因此这句话便有他的族人没有死完的意思在,彭士愁是其子便是成立的。
我们对“所部”的理解应为“所率领的救援军队”,因为去千里之外救援解围,要求日夜奔袭尽快抵达,不可能把妻儿老小都带着,作为能征惯战的刺史,一定会只带健步如飞、行动迅速的士兵,从“楚兵救瑊,虏骈以归”(《资治通鉴·后梁纪·二》)中,也可知彭瑊救援行动太快,与后续部队严重脱节,反被包围,不得不再由后来的楚兵大部队来救,结果是彭瑊及赤石的老小与所率领到此的部队全死、死后不久敖骈被俘,彭瑊留在辰州的家小及守护人员则得保全。有人对其家小到辰州去了一部分表示怀疑,可用《资治通鉴》(卷267)中的“开平三年……玕帅众数千人奔楚”、《宋史·刘沆传》中的“玕胁迫百姓数千家入湖南”、宋代龙衮《江南野史》卷六(大象出版社,《全宋笔记》·第一编·三)《彭玕传》中的“与兄弟唱召义师,以自卫乡党为名,得勇力无赖五百余人……因尽掠百姓户口几千余家入郴衡……兄弟皆涖县邑……惟玕之子孙耻而不返”等记载释之,即这数千家中自然包括了彭瑊的一些家人,其兄弟(当然包括彭瑊在内)都在县里为头目,他们的子孙留在了湖南(其后代的后代也有回了江西的)。同时也可分析,作为辰州刺史不可能不留一些军政人员及家属坚守岗位、保护辖区,而留在辰州的家人即彭士愁他们。
从上下文的思路上看,若是彭瑊全门都死光了,一个后人都没有了,那么这《楚纪》后面的文章就应写在别人的祖先之后,根本没必要作为彭士愁及其后裔的祖先写在彭士愁的前面——作为进士出身及侍讲学士的廖道南这点逻辑应是有的。
我们对这里的“厥后有”三字也应准确理解而不能忽视或歪曲,这三字译为现代汉语是“其后有”“他的后裔中有”的意思,再后面承接的是古文中常见的举例句式“有……有……有……有……”,其意思是十分明了的,即他的后代中有彭构云,有彭玕、彭瑊,有彭士愁,有彭儒猛。这就很明确地写明了湘西彭氏土司主是来自江西。
当然,在湘西彭氏司主的碑、铭、谱中,也有记载自己的历史是自汉、唐以来就一直在湘西一带为国效力,似与彭瑊入湘西矛盾,这可以理解为其后人与当地土著深度融合后对中原的历史文化知识学习掌握得少而将五代的唐、汉错误地理解为五代之前的汉、唐了,或吹嘘夸耀,但不能以此否定明永乐以前国家的史籍、文献及相关记载的正确性。
至于有人将陆游《南唐书》中的“师暠不知其世家”理解为“彭师暠不知道他的世代传承情况”,而证明彭师杲(即陆游笔下的师暠)是如原始社会的土著连自己的世代传承都不清楚的人,而否定其来源于江西之说,就更不必多去计较了,只提点一下:这句话是陆游说自己查了不少史料不知道师杲的祖上传承情况,而不是彭师杲不知道自己的祖父及曾祖高祖是谁。因为铜柱上记其“为父输诚,束身纳款”,纳的是“本管诸团百姓、军人及父、祖本分田场、土产”,是他将“父、祖”的田场、土产这些都抄好后送给了马氏,他怎么不知道自己的父祖名字及世家呢?从此传及“铜柱”文中可以看到彭师杲是很有见识和文化修养的武将,不是原始社会的土著。“廖偃师暠之事,可谓尽忠所事者,而《五代史》以为马希崇遣师暠偃囚希萼,而师暠奉希萼为衡山王,是偃亦同受囚希萼之指,而师暠独能全之也……大抵忠于故君,两人实同,而偃功为多,不可诬也”,显示彭师杲是个受汉文化熏陶很深的忠诚、厚道、勇武之人。
还有,有人说彭师晏“举族为诸酋所杀”被“另外一支溪州彭氏”取而代之、这支彭氏是永顺州彭氏而非下溪州彭氏,从而怀疑彭瑊与彭士愁的父子关系乃至血缘传承关系进而歪曲为义父义子关系,以及代代抄袭、引用错句“溪峒州……皆盘瓠遗种”(里耶秦简、三国志、两晋、南北朝及隋唐史等均记载有不少人入溪峒),“凡蛮即非汉人血统”,诸如此类,就更
不值一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