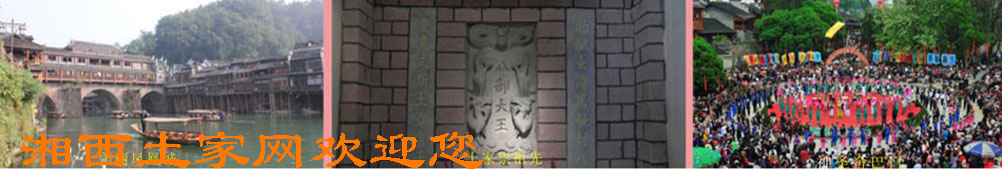湘西保靖的土家族民俗村:亨章村
田二文
“锦鸡飞过彩云岩(ai),收拢羽毛落山寨。远方朋友远方客,欢迎来我土家寨。”
我们是在村民们的迎宾歌声中来到亨章的。村口的高大路标石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头戴不少光环的湘西乡土,“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全国生态文化村”,任何一块牌子都折射出村庄的含英咀华和任时光淘洗心质不改的典雅稳重。800多人的乡野僻地“口衔三玉”,在保靖县乃至湘西州都不多见。
从保靖县城出发,走20公里县道迁普公路到桐木枯,这是个土家语地名,意思是长满泡桐树的山堡。从桐木枯往左,通村公路沿小溪逆流而上,弯弯绕绕4公里,抵达村文化广场后,路戛然而止,形成钻进“口袋”的断头路,这里已是村庄的纵深,也是村部这一基层政治舞台的所在之地。
从村部上行两里,小溪源头赫然在目,猫儿心瀑布飞珠溅玉,甩入浅潭,漫溢而流,贯穿古寨,绵延七里,犹如一幅巨大油画展陈在天与地的缝隙中,被人们贴切地冠上美名——七里溪。水利万物而不争。逐水而居的彭姓人们将家安放在七里溪两岸,一栋栋依山傍水的木质建筑竖立宁谧安详,年年岁岁;房前阡陌田畴平染河雾水烟,岁岁年年。鹤立鸡群的吊脚楼唤取人们关于“小背篓晃悠悠,笑声中妈妈把我背下了吊脚楼 ”的生命早期的香醇记忆。
亨章系土家语。这里路边的土坎上常现月牙形的半圆小平台,供人们停放背笼,暂时歇气,此等小平台便是土家语亨章的专业解释。这一语言现象牵扯出保靖土家彭姓在深山背肩磨脚、繁衍生息、瓜瓞绵延的峥嵘与苍凉。
湘西彭氏土司800年的荣光,不可或缺香坛土司的一抹霞彩。像一粒飘落的种子,又或像一群分家的蜜蜂,从湘西土司王国或土司王朝治下诞生出的香坛土司,起根发祖就在这五谷峰下大山切谷的悠悠亨章。
十代、二十代人的胝肩茧足、积极创造,砌坎垒岩,挑沙填土,成就亨章一坝坝嘉穗盈仓的立命良田;十代、二十代人的埋骨青山、融入尘土,留下亨章一处处追思肃祀的人文遗迹。一代代土王,也即实际意义上的血脉祖先,像划过长空的流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绵密痕迹,构成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朽素材。村口的香坛庙遗址飘浮着一个个土王,即一位位列祖列宗的雄武远影,散落于蓁蓁荒野之中,调和彭氏子孙黏稠的精神皈依。
长城一样的石头墙忠实地护卫着彭氏祠堂旧址。祠堂建于1937年,毁于“文革”期间。凛冽的石碑上,勒记着彭氏土司一脉辗转迁徙来到亨章的艰辛经历,昭然彭氏六十字辈的恒久常转,灵动彭氏儿女“水有源头人有根脉”的感慨心声。
山里巨大封土堆下的土王墓用一份神秘、一份神圣,搅动人们的好奇之心,挑起人们的探索意志。一次浅尝而止的考古发掘,发现墓室多进,每进8尺,并列两道门,门有栓子,十分牢固。传说墓深48进,真相如何,只有等到古墓完全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岁月漂白了墓主人的身份密码,未晓姓名,不知几代。然而,一则讽刺故事道出他的弄巧成拙:土司王长子性格刚烈,总是与土司王对着干。土司王说东,长子说西;土司王说白,长子说黑。临死前,土司王怕死后儿子不让自己入土,故意说反话,说自己怕入土,喜欢棺木悬空。土司王死后,儿子想自己一辈子与父王不和,现在父王死了,一定要遵从他老人家的心愿,做到问心无愧。于是叫人用四根大铁索把土司王棺木悬挂在坟墓空中。真个人算不如天算。
寨中躺平在苍松翠柏环抱中的文昌阁遗址,让人穿越回到过去读书习文的开化时光,耳旁响起那“入云高阁福亨章,古风今韵放华光。地灵千秋育才俊,人杰万代颂文昌”的飘逝诗家绝唱。
亨章村无论男女老少,人人能歌善舞。摆手舞、毛古斯等土家歌舞和打溜子、咚咚喹等土家乐器,他们烂熟于心,信手拈来。村里至今还盛行抵杠、蛤蟆抱蛋、踩高脚、舞狮、玩龙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每逢节日喜庆,男女老少均穿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欢庆,好一个民族团结、和睦发展图景。
当幻想中的桃花源早已成为古典文学语境下的理想生活场景,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差太远,终究显得有些时过境迁时,亨章古寨以其客观的现实存在而成为一处现代人可以找回过去和安放灵魂的精神家园。
亨章人扯住原始美的衣角,擦亮三大国字号品牌。以“品土风古韵、享自然之美”为指向,积极打造集山水观光、民俗体验、特色种养、餐饮娱乐于一体的乡村旅游,逐梦文旅融合发展旗帜猎猎。
|